匍匐大地的“荒漠拓荒者”——阿不都拉·阿巴斯傾注半生心血研究新疆地衣

11月15日,阿不都拉·阿巴斯在昌吉市硫磺溝鎮採集地衣標本。
在荒蕪的山間,隱藏著微小而神秘的生命——地衣是附著在岩石表面肉眼可見的生物,其生長中產生的地衣酸可對岩石表面進行生物風化,形成硬化的基物,變為土壤層,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存創造生長條件。地衣可覆蓋荒漠表面,改變沙土流動環境,因此被譽為“荒漠拓荒者”。
地衣也是檢測環境污染的“排頭兵”,它們對污染物高度敏感,在二氧化硫濃度過高的區域無法生存。此外,地衣還是重要的生物資源,中國已知可藥用、食用地衣就有130多種。它們具有降血壓、止血消炎等藥用價值。
新疆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阿不都拉·阿巴斯研究地衣用了半生時光。
是科學家,也是非遺傳承人
滿頭銀發,戴著黑框眼鏡,頭頂鴨舌帽,身披咖色夾克,帶著放大鏡、GPS、相機、標本袋等設備,阿不都拉像一位走入自然的偵探。冬日的一天,他乘車前往昌吉市硫磺溝鎮,開始一天的“地衣尋訪之旅”。記者跟隨他共同“走進”這個微觀世界。
“地衣和苔蘚的形態相似,它就是苔蘚嗎?”面對記者的疑問,阿不都拉認真地說:“地衣並不是植物,它是一種共生藻和共生真菌組合而成的真菌。在自然界中分布著殼狀、葉狀、枝狀3種地衣類型,它們形態各異,各有特色。”
當車輛行駛在S201省道時,朝陽映在連綿起伏的山丘上,初雪多了幾分色彩,宛如童話世界。
“蘇師傅,這地方不陌生吧?”阿不都拉問司機,拿出相機拍攝路牌。“拍路牌是我們的科考慣例,留下痕跡,証明我們曾來過。”司機蘇新明是阿不都拉的“老伙計”,每每野外科考,他會駕車與阿不都拉一同前往新疆各地採集地衣標本。
“和阿老師去的地方多了,我也能分辨地衣的種類。”蘇新明說。
車輛駛向山間深處,急彎越來越多。
“蘇師傅,停車。”阿不都拉取出設備走向大小不一的岩石,隻見幾塊紅色、綠色的地衣附著在上面。他蹲下身子,手持放大鏡,俯身靠近石塊觀察。“是葉狀地衣,看來這裡空氣還不錯。”阿不都拉取出相機,將鏡頭貼近地衣,拍攝下幾張照片,接著拿起挂在脖子上的GPS設備,按下幾個鍵,數字躍然而出。“GPS數據能快速記錄地衣分布的經緯度信息,便於歸類整理。”說完,他放下相機,取出鐵錘和榔頭,小心翼翼地對著石塊側面鑿去。他慢慢取下附著地衣的石片,細心地用紙巾包裹地衣,然后放入野外採集標本袋中,用橡皮筋纏繞妥帖,便完成了地衣標本採集。
連續採集兩個小時后,阿不都拉坐在岩石上歇息。他從背包裡取出幾塊蜂蜜餅干,說:“這也是我的裝備,野外考察最消耗體力,需要經常補充能量。”
阿不都拉還是一位塔塔爾族傳統糕點非遺傳承人,經常親手制作各種糕點,與親朋好友分享美食。“2012年,塔塔爾族傳統糕點制作技藝被列入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同時我被認定為該技藝自治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他說,“小時候,每周媽媽會做兩次糕點,我總是在旁邊打下手,慢慢地掌握了糕點制作的訣竅。工作后,我仍然保持著每周制作一次糕點的習慣。親朋好友相聚時,它是最好的美食。”
吃完餅干,他拍拍手,拾起鐵錘和放大鏡,繼續穿梭於斑駁的岩石間,搜尋地衣。
十幾張存儲卡,濃縮幾十年科研印記
阿不都拉的家裝飾典雅,但他的書房卻別有洞天,仿佛是一個記錄自然的秘境。隻見電腦桌邊堆滿了書本,形成一個龐大而有序的書山。十幾個箱子裡裝滿了密密麻麻的地衣標本。阿不都拉介紹,採集的標本都封裝在正規的標本袋裡,上面寫著地衣種類名稱、分布區域、經緯度、採集人、鑒定人等。每一個字,都是他仔細核對后親手寫上或打印貼上。為地衣制作“身份証”,已成為他的重要工作。
當阿不都拉拿出從南山採集的新鮮地衣標本,兩隻小貓好奇地嗅著地衣標本袋,宛若兩個“小助手”。
“地衣結構復雜,解剖起來也復雜,還要制作切片,通過實驗來斷定。”阿不都拉介紹,在鑒定新品種時,需根據地衣特性,運用觀察形態結構、解剖結構、顯色反應、微量化學結晶、薄層層析等方法,還需做分子DNA片段測序才能得到最終結果。
當地衣標本置於生物解剖鏡下,阿不都拉目光專注,尋找每一個微小的特有附屬結構細節。在他身后,一台用壞的解剖鏡靜靜地立在桌面,默默見証他專注地衣領域研究工作的時日。
“我電腦上文件夾就像一本地衣詞典。我為每張地衣照片都做標簽化工作,在檢索時隻需輸入相關信息,就能迅速找到對應的照片。”如此嚴謹的工作態度,離不開阿不都拉在求學期間打下的良好科研基礎。
我國地衣研究起步較晚,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由魏江春院士帶領科研人員展開。起步晚、資料有限、人手不足成為地衣研究者面臨的困境。
1976年,阿不都拉從新疆大學畢業后選擇留校任教。1990年,他來到南京師范大學進修學習,師從著名的殼狀地衣專家吳繼農教授。1993年至1995年9月,他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魏江春院士國家級實驗室深造,研究地衣生物學3年。
阿不都拉逐漸認識到,研究地衣在我國生物學領域具有重要意義,“新疆是豐富的天然地衣生物的基因庫。地衣是自然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既是生物多樣性的具體體現,也是生態系統穩定性的重要保障。”
1995年,學業期滿,阿不都拉回到學校,繼續深入研究地衣。“那會相當困難,缺少儀器設備,有關中國地衣的研究資料匱乏。”他開始重視地衣標本的採集,以期得到新疆地衣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在阿不都拉的書桌上擺放著一摞存儲卡。做完實驗后,他通常將照片資料拷貝至電腦,用中文與拉丁文備注採集信息,導入文件夾中,並建立描述特征的電子版文件。他說:“卡裡存儲的都是地衣照片,大概20萬張。”
十幾張存儲卡,是阿不都拉幾十年的科研印記。
阿不都拉2018年退休后,每年還會進行三到四次野外考察。“趁著我還能走能跑,我想盡最大努力將新疆所有的地衣都研究一遍,這是我畢生的夢想。”他說。
我的墓前會擺上地衣
“退休前,我和自己培養的碩博研究生共同採集研究,發現了30種新種地衣,文章被SCI收錄,地衣基因組全都錄入世界基因庫。”阿不都拉自豪地說。
山高路遠,難以為繼。多年來,阿不都拉帶領學生輾轉於天山、阿爾泰山、昆侖山等地。每當發現未知的地衣時,他認為,這漫漫路途是值得的。
“有一次在阿爾金山考察時,疑似發現新種,我激動得手都在抖,小心翼翼地保護好標本,帶回實驗室研究分析后,確定是新種,大家都長舒一口氣。”阿不都拉笑著說。
多年野外考察,也讓他們數次陷入險境。“1980年,我們帶一個班的學生在喀納斯湖西南部的山頭採集標本,歸來時,被一隻狗熊尾隨。”阿不都拉點燃火把走在隊伍末尾,最終安全脫困。此外,在崎嶇山路上摔倒磕傷也是家常便飯。“對於我們新疆大學‘中國西北干旱區地衣研究中心’團隊來說,這些困難遠不及每次發現新種地衣時的喜悅和成就感。”阿不都拉說。
從事地衣研究的樂趣,也在學生們心中留下難忘記憶。2003級植物學碩士生劉麗燕至今難忘那段時光:“我們和阿不都拉老師一起外出採集地衣標本時,可以品嘗到老師親手制作的塔塔爾族傳統糕點。”畢業后,劉麗燕進入新疆林科院造林治沙研究所工作,“盡管我現在不從事地衣研究,但是那段科研時光為我今后從事荒漠化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2010級博士生古麗波斯坦·司馬義看來,阿不都拉嚴謹的科研態度對她產生了深遠影響:“阿老師是我碩博學習階段的導師。每當我想放棄科研時,他都會鼓勵我,給予我實驗指導。”如今,古麗波斯坦在新疆林業規劃院工作,“十余年的求學生涯,讓我的研究范圍擴大到沙漠化治理。每到一地,開展地衣研究實驗,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新疆地衣資源豐富,但相關研究較少。“我編寫的書籍《新疆原色地衣圖譜》,明年能出版發行。”阿不都拉介紹,這是一部科普性專著,可為地衣研究者、高等學校植物學科選修課的學生以及地衣愛好者提供參考。
流沙漫卷,歲月蹉跎。43年的地衣研究,無數人問阿不都拉,研究地衣分文未掙,有何用?“他們都說我是傻瓜。”阿不都拉笑著說,“如果離開地衣研究,我會感到人生失去方向和意義。”
思及此,阿不都拉神情嚴肅,緩緩道出心底的願望:“我離世后,家人會在墓前擺放一片岩石上長滿地衣的標本,作為我對這段熱愛之旅的延續吧!”那些小小的生命,承載著他畢生心血。
延伸閱讀
地衣是件什麼“衣”
地衣作為新疆地區的重要地被類群,對改善干旱及半干旱生態環境和天然草場環境發揮重要作用。新疆早期研究地衣時,隻有68種地衣種類被定名,如今已達650余種。
地衣(Lichen)是希臘植物學家Theophrastus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寫入希臘圖書材料中。Theophrastus將地衣粗略地描述為一種生長在橄欖樹皮上的植物。過去和現在部分地衣被稱為古老的草藥。16世紀初有些地衣種類被描述有醫學上的作用。法國植物學家德堪多從植物分類學的角度把地衣納入一個屬名中。
地衣生物是真菌類及藻類或藍細菌長期共生形成的,是一種穩定復合有機體的地衣化的真菌。地衣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界生物物種多樣性的一種主要體現。新疆的自然環境比較復雜,遠離海洋,有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干旱的大陸性氣候特征,這裡有世界著名的山脈、永久性的冰川以及雪山,高山上有寒冷的荒漠、原始森林、天然的草原,平原中的盆地、沙漠、荒漠、戈壁,山系和荒漠中的河流、湖泊、沼澤地等多種自然景觀以及復雜的多種多樣的地理及地質構造,為地衣類群的生長提供了豐富的生存環境。
地衣在准噶爾盆地沙漠地帶形成大面積的結皮,對保護新疆干旱生態系統多樣性、治理沙漠、改善荒漠干旱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研究新疆地衣類群以及地衣中的菌類和藻類的共生關系,可為新疆地衣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供科學理論和實踐性研究依據。(宋海波)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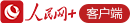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